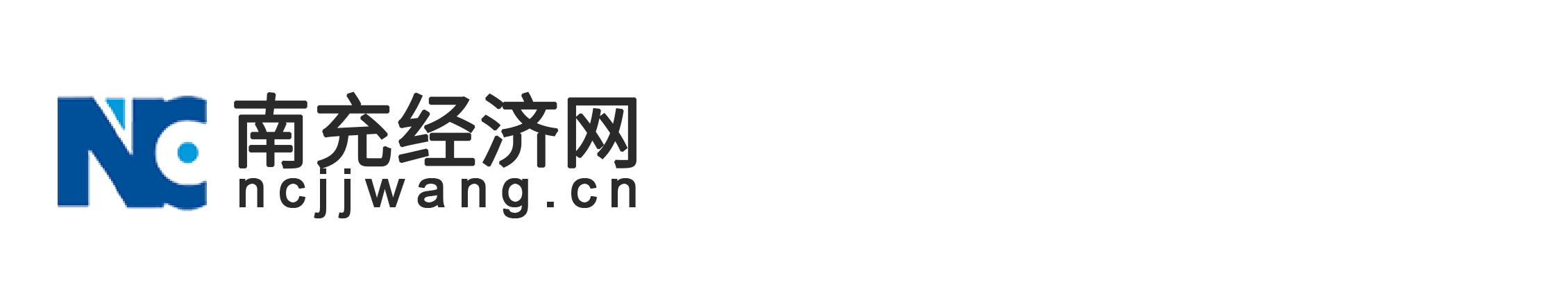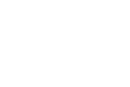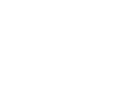吴迎春(顺庆)
周末,女儿从老家后院的泥土里挖出一块石头,嚷嚷着要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挖着古董了。待我走近一看,原来是一堆石碾、石磨等破旧石器,不知何时被掩埋在了屋后的泥土里,石器上的横纹早已辨不清模样。但是,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过年的味道。
打我记事开始,春节杀年猪、磨豆腐、打糍粑等都得靠老家这堆石器来完成。屋外院子里的厚石墩,是院子里邻居杀年猪的专用。父亲看好日子,便通知叔伯们等着。杀年猪这天,院里就是家族式聚会。大人小孩围在一起,按猪的,拿盆的,烧水的,大家忙前忙后,各司其职。
中午的杀猪饭是一天的重点。这天,一大家人聚在一起,一边分享美食,一边谈论当年的收成。石墩旁的热闹在猪肉的香气里慢慢趋于平静,石磨开始登上舞台。
那时,左邻右舍提着泡好的黄豆到我家磨豆腐。心地善良的母亲热心助人,邻居家推磨人手少时,她就开心地帮人家推磨。沉重的磨子连接着磨盘,得两个人一起才能推转。另外,一人拿着扫帚把磨子中蹦出来的黄豆扫到磨洞里,磨盘转动的“嘎吱”声混着邻里间的谈笑声响彻小院。随着磨子的转动,一股股豆汁顺着磨盘流进石缸,浓郁的香气和着邻里的和气又添一丝年味。
真正带给我欢乐的并不是腊肉与豆腐,而是除夕夜的糍粑,母亲提前用温水将新鲜的糯米泡上几个小时,泡好后倒进木甑子,加水稍微没过糯米,烧大火把糯米蒸熟。
母亲一边控制火候,一边凭着经验判断糯米的情况。我跟在母亲的屁股后面,只要母亲一起来,我就忙探着脑袋询问:“妈,好了吗?”“还没呢。”母亲一边观察锅里的水位和冒上来的蒸汽,一边回答我。
我对母亲的话表示质疑,想掀开锅盖看看糯米的样子,母亲阻止道:“蒸制糯米时,中途揭开锅盖会影响糍粑的香气。”为了吃到香甜软糯的糍粑,我只好又蹲回灶门口,闻着锅里的香气,等母亲最后一声令下。
打糍粑最具挑战性的就是舂打的过程。蒸好的糯米放进两尺见方的碓窝里,父母各持一根木槌充当“打手”,铿锵有力地敲打糯米。
打糍粑的过程并不干净利索,木槌砸下去,柔软厚实的糯米团紧紧地贴在木槌上,随着木槌地起落发出类似“嘭”的声音。母亲则弯腰用短木槌按住糍粑,等父亲直起身子配上特有的口号,再次发力时,母亲再取出木槌。在儿时的我眼中,他们更像是在表演木偶戏。我和弟弟也加入这场表演中,两尺宽的碓窝边,上演了一场四人大战。碓窝里的糯米被拧起、捶打,缩成一团,紧紧地抱着木槌不撒手。倔强的样子,差点让我笑岔气。为此,母亲总会瞪我一眼,说我没有半点女孩子的样子。舂打好的糯米变成了细腻的糍粑,母亲将糍粑一分为二,一半沾上白糖,被我和弟弟吃进肚子里;一半放在簸箕里压成椭圆形的厚饼晾晒,再切成片,留着过年吃。啃槌棒是每年打糍粑必不可少的环节,总觉得沾在槌棒上的糯米更有嚼劲。偌大的木槌与娇小的我们形成鲜明的对比,这一贪吃的形象却成了母亲经常提及的笑柄。
汪曾祺先生曾说: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当新年来临时,左邻右舍一起互帮互助,共享美食的愉悦,便是赶走寒冷的良药。前几天母亲又打电话说:“腊肉、豆腐已熏好,就只剩糍粑未打,等我放假和弟弟一起,打好后好提前给叔伯和邻居送去。”
在母亲的世界里,她依旧用最传统的方式在迎接着春节的到来,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墩、石磨、碓窝虽已随风远逝,但新年时期望家人和睦、安康的习俗却永远传承。